

我喜欢这紧张的中间状态,我感激生命为我提供的这变化的可能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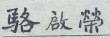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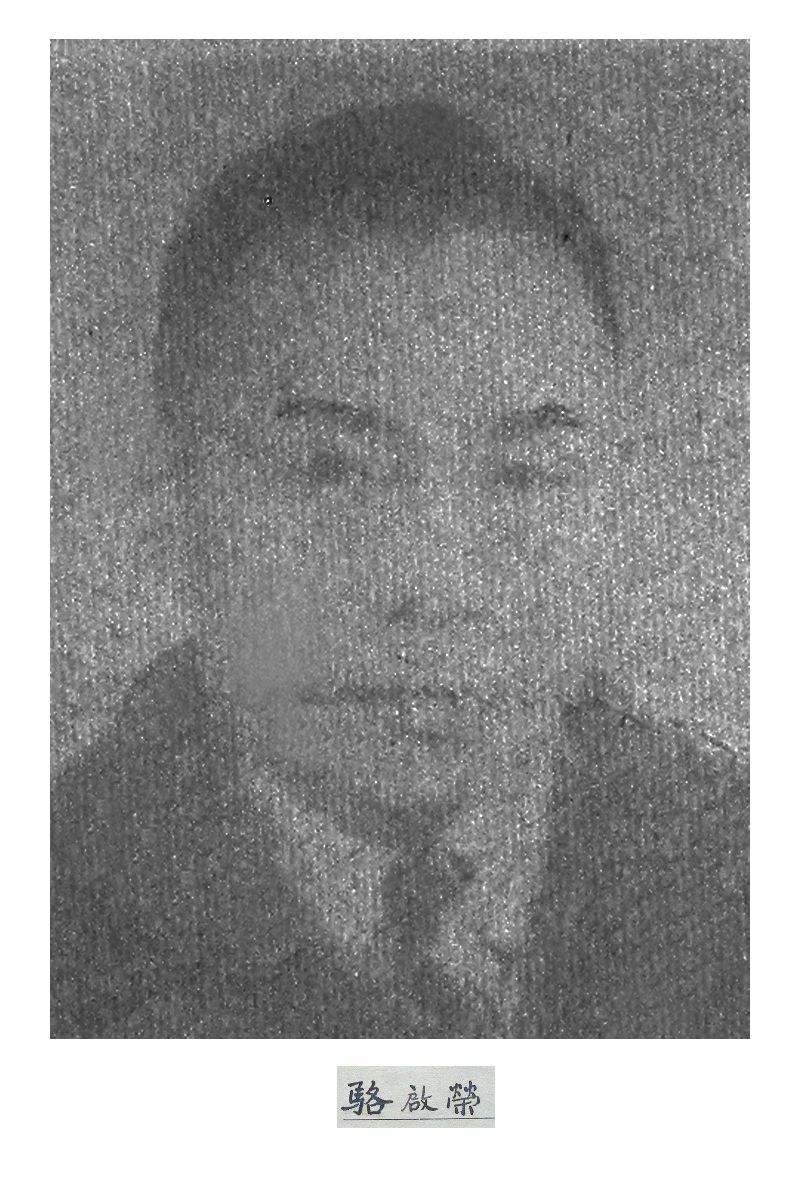
骆启荣(1900.12-1981.3),四川郸县人,鱼类学教授。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,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、斯坦福大学,获生物学博士学位。曾任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校长,四川大学、华西协和大学、西北大学、暨南大学等校教授。曾在清华学报发表《二十年来中文杂志中生物学记录索引》,收录生物学文献1000篇;编写《西印度群岛鱼类志》刊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刊。
追求科学,热爱科学
父亲对骆启荣的教育以启发为主,不墨守成规,因此骆启荣自小就养成思维活跃,以理服人的习惯,有时与父亲也会展开争论。骆启荣说:“这样的父子关系让我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,让我凡事敢于质疑,很小就喜欢高谈阔论,甚至有点想入非非的味道。这自信与率直的性格,是父亲给我的最大礼物。”父亲去世后,兄弟们开始分家过日子。失去了可靠学费来源的骆启荣,听说清华学校不收学费,就决定一试。
清华学校是清政府用列强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,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。当时考入清华就意味着获得国外留学机会。骆启荣是庚子年(1900)出生的,似乎与清华园有某种缘分。1916年他顺利考取清华学校,与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、著名文学家朱湘等都是清华甲子级同学(他们都于1924年毕业,1924为农历甲子年)。他与山西同学,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冀朝鼎,尤为亲密。
由于列强横行,军阀割据,政治昏暗,民生凋敝,在清华学校读书的莘莘学子,纷纷选择了自己的求学报国之道,有的选择“科学救国”,有的笃定“实业救国”,有的主张“教育救国”。骆启荣在清华园里博览群书,渐渐对生物学发生兴趣。他甚至在参加清华学校泰西文化班之余,自己选定图书馆的15种中文杂志,利用东京丸善株式会社生物学分类表,梳理了1000余篇关于生物学的文献索引,并撰写《二十年来中文杂志中生物学记录索引》一文。这篇文章于1925年发表于《清华学报》。骆启荣爱上了科学,自然而然选择了“科学救国”。
骆启荣热爱科学,兴趣广泛,他的篆刻在清华同学中颇有名气。在同学朱湘写给闻一多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,“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,有骆启荣君担任雕刻,有吾兄及杨廷宝君濡写壁画,有余上沅君赵畸君开办剧院,又有园亭池沼药卉草木以培养实秋兄沫若兄之诗思,以逗林徽茵女士之清歌,而达夫兄,年来之悲苦亦得藉此以稍释,不亦人生之大快乎”。朱湘所言雕刻,其实是指篆刻,由此可见骆启荣的才艺。
1924年,骆启荣从清华学校毕业后,与同窗好友冀朝鼎,一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。骆启荣主攻生物学,冀朝鼎学习的是历史学。值得一提的是,1941年他曾受冀朝鼎之邀,在重庆担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处主任。此时,冀朝鼎已是中共地下党员。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,骆启荣力尽所能多次给予冀朝鼎大力协助和掩护,确保了冀朝鼎工作的正常开展。冀朝鼎是1927年从美国赴欧洲开会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解放后,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,全国第二、三届政协委员等。
在芝加哥大学,骆启荣并没有局限于学习生物学,而是广泛涉猎各种学科,如地质学、经济学等。他希望了解各个学科的概貌和发展状况。芝大前沿的学术信息,宽松的教学氛围,良好的研究环境,使骆启荣沉浸在科学的店堂里兴奋不已。四年的学习,使他渐渐对鱼类学产生浓厚兴趣。
骆启荣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后,经导师推荐于1928年3月转赴斯坦福大学攻读动物学博士学位,主修鱼类学和无脊椎动物学。斯坦福大学位于美国西海岸,是世界著名大学,今天更因硅谷而声誉雀起。在斯坦福,骆启荣参加了西印度群岛的鱼类调查研究工作。期间,他克服水土不服以及语言文化差异,在西印度群岛搜集、鉴定鱼类标本,基本摸清了当地鱼类资源状况,并发现一新属,命名为Halieuticur burbradeusis(Genus Holiuticus)。1930年骆启荣在斯坦福大学校刊发表《西印度群岛鱼类志》并获生物学博士学位。
在美留学期间,骆启荣还留下了一段热心助学的佳话。我国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,两院院士罗沛霖就曾得到骆启荣的关心。罗沛霖的父亲罗朝汉,曾以墨绘竹兰石及文物鉴赏在北京颇有名气。骆启荣因喜篆刻,与罗朝汉接触比较多,也因此认识了比他小13岁的罗沛霖。骆启荣到美国后,常给读中学的罗沛霖寄些英文无线电杂志和物理化学手册。罗沛霖收到杂志后借着英汉词典研读,对无线电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。后来,他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并获博士学位。
从事科学,献身科学
骆启荣回国后,先后担任天津河北水产专科学校校长、河南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华西协和大学、西北大学等校教授。抗战胜利后,他到上海暨南大学,任经济学专任教授,讲授《商用英文》、《英文会话》、《商业心理学》等课程。1949年春骆启荣没有随暨南大学南迁至广州,而是先后出任中央食品工业部参事、中央农业部参事,后又因工作需要调至河北省立水产科学校任教授兼养殖系主任。
1953年8月河北省立水产科学校并入上海水产学院,他随校来沪。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,亟须发展科学事业。骆启荣开始围绕国家建设需要,着手编写《中国食用鱼类》第一部、《淡水鱼病害》等著作。由于留学多年,骆启荣英文流利。1960年4月在他60岁之际调至由朱元鼎于1958年成立的东海水产研究所编译室作研究员,翻译英文科学文献,直至1963年10月退休。
骆启荣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生物学打交道,是一个很开明的人。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医学事业,在患不治之症于弥留之际,他握着妻子唐淑清的手动情地说:“我死后就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用,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吧。”直到妻子含泪点头答应,他才满意地合上眼睛。1981年3月31日,这位可爱的老人离开了我们。妻子遵其遗嘱,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上海第一医学院(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)。今天在上海福寿园红十字遗体捐献纪念碑上,“1981年实现捐献者”那一栏镌刻着两个名字:骆启荣和丛培基。骆启荣从事科学,身后又献身科学。他是上海市第一位志愿遗体捐献者。
骆启荣的事迹被报道后,电台、报社收到大量群众来信,纷纷赞扬这种献身科学的行为。中国文化比较看重死有所葬以及遗体完好,对1981年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人来说,志愿捐献遗体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事。骆启荣从事生物学多年,深知遗体对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。他破除陈规,首开先河,志愿捐献。之后,上海市红十字会、市卫生局与上海第一医学院等合作,筹建了上海第一个志愿遗体捐献站,于1983年1月1日正式接受市民报名登记。截止2006年底,已有23578位市民自愿登记加入遗体/角膜捐献志愿者行列,有3942位志愿者实现了捐献。在捐献者中,年龄最大的110岁,最小的才两个月。如果先生有灵,他可以含笑九泉了。今天上海的医学事业已蒸蒸日上,抚今追昔,骆启荣当年之举无疑具有开创意义。
(生命学院 马若群)

